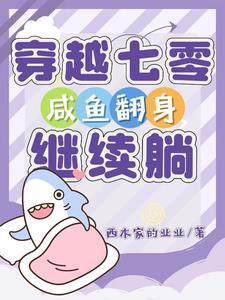我去读小说>回溯刑警破黑局风云 > 第172章 抽丝剥茧寻真相(第1页)
第172章 抽丝剥茧寻真相(第1页)
我盯着电脑屏幕,两份文件并排打开,手指悬在键盘上半天没动。显示器的蓝光冷冷地打在我脸上,像盖了一层霜。窗外黑漆漆的,整栋办公楼就我们这间技术室还亮着灯,走廊尽头的应急灯闪着微弱的绿光,安静得让人心里紧。
我们一直在等周临舟出现,可一整夜的监控画面死寂一片,c栋像个被遗忘的老楼,连风刮过都带着空荡荡的回响。外墙斑驳,几扇窗户碎了也没修,风吹进来,吹得里面的机柜出“呜——”的轻响,像是谁在低声哭泣。摄像头稀疏,西面更是大片盲区,仿佛那堵墙天生就藏着秘密,不让人看。
时间慢得像爬。凌晨三点十七分,我揉了揉酸胀的太阳穴,端起桌角凉透的咖啡喝了一口,苦味直冲喉咙。李悦坐在我斜后方,戴着耳机,手指在触控板上来回滑动,嘴里小声念着代码。她已经连续工作十六个小时,眼底青,但眼神依旧亮得吓人。赵勇靠在门边打盹,军绿色外套搭在肩上,呼吸平稳,可只要屋里有点动静,他眉头一皱,立马就醒了——那是反恐队留下的本能。
“还没信号?”我轻声问。
李悦摇头:“服务器日志全被清过,碎片也被加密擦除。这不是普通删除,是专业级的数据销毁。”她顿了顿,嘴角忽然扬起一点笑,“但……不是完全没有痕迹。”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再完美的系统也会有漏洞,就像雪地上走过的人,哪怕扫平脚印,体温也会让雪化得慢一点。
天刚蒙蒙亮,六点整,晨光从百叶窗斜照进来,在地板上划出一道道灰白条纹。突然,李悦来消息:“有现!”声音不大,却像一颗石子砸进水面,激起涟漪。
她说在临江物流公司的服务器深处,抓到了一段异常的数据流。那不是正常的业务数据,而是一串伪装成备份的小包,每隔四十八小时悄悄上传一次,每次不到三分钟。藏得太深了,嵌在正常传输里,要不是她用了自己写的流量分析程序,根本现不了。
正说着,赵勇走过来,递给我一杯热水,什么也没说,轻轻放在桌角。“嗒”一声,杯子碰上木桌,清脆又轻微,像是时间重新开始流动。
我抬头看他一眼,他冲我点点头,转身去泡自己的溶咖啡。我没说话,只是握紧了手里的杯子,暖意顺着掌心一点点蔓延上来。这种时候,话太多反而多余,默契才是最珍贵的。
屏幕上蓝绿色的字符还在滚动,像一条不停流淌的小溪。李悦正用逆向追踪技术,一点点拼回那些被删掉的日志。这些碎片,正在慢慢连成一条路,通向某个看不见的黑暗角落。
她调出解码界面,输入一串复杂的密钥,随后,一行行被覆盖的访问记录浮现出来:境外ip地址:,连接时间:o:o-o:o,协议类型:ssh+tls隧道加密,目标端口:……
“又是这个ip。”我喃喃道。
这个ip断断续续出现,但规律得很,每次都选在凌晨两点到四点之间上线,持续不过八分钟,像有人定时打开一个秘密频道。更奇怪的是,所有连接都指向同一个虚拟主机节点,登记地在塞浦路斯,实际通过多重跳转隐藏真实来源。
“这人不简单。”我低声说。
声音不大,但屋里的三个人都听见了,空气一下子凝住了。
赵勇放下杯子,走到屏幕前,盯着那串ip看了几秒,缓缓点头:“能在军工系统混过,还能对接暗网,这种技术不是自学能有的。肯定是体制内出来的,手里有资源,脑子里懂架构,更知道怎么绕开监管。”
他说得很平静,语气甚至有点冷,但我看得出他心里已经拉响警报。他是反恐总队出身,经历过边境黑客案、内部泄密事件,对那种“背叛体制”的人特别敏感。那种人最可怕——他们懂规则,所以会钻空子;他们曾被信任,所以更擅长伪装;他们清楚每一个安防节点的弱点,就像熟悉自家门锁一样。
我们决定重新梳理所有线索。
我把c栋的建筑图纸调了出来。这是园区最老的一栋楼,建于九十年代末,原先是仓库,后来改成临时数据中心。墙厚、隔音好,但监控老旧,西边一大片盲区。晚上保安松懈,外来车辆进出基本没人管,想查清楚太难了。
只能靠外围信息一点点推时间线。
我翻出最近七天货运枢纽的车辆记录,重点筛没登记的皮卡和厢货。etc数据显示,一辆深色无牌皮卡在三月二十日凌晨一点十七分进了园区西侧便道,停了四十三分钟才走。车斗是空的,但称重系统显示整车自重比正常高出快三百公斤。
“运的是设备。”我说。
李悦放大卫星图,指着便道尽头:“你看这里,靠近c栋后墙有个废弃检修口,平时没人走。铁栅栏本来锈死了,但最近被人撬开过,边缘有新鲜刮痕。”
她调出热成像回放:凌晨一点五十六分,检修口方向出现了短暂的热源波动,持续大概五分钟,然后消失。虽然看不清人数,但从移动轨迹判断,至少两个人一起搬东西进去。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我把这个时间记下,转头对赵勇说:“你去趟园区,找夜班保安问问。特别是那天凌晨值班的,看有没有人见过这辆车,或者看到谁搬东西进去了。”
他二话不说,抓起外套就走。临出门前回头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后只留下一句:“别熬太晚。”
门关上后,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空调低鸣,服务器风扇嗡嗡响,李悦继续埋头分析数据流,而我则翻起了电力申请档案。
那个叫“张林”的临时用电申请人,身份证号居然是个测试用的备案码——假身份。手机号也注销了,运营商显示最后一次通话是在两周前,地点在城南工业路一带。
不过申请单上留了个手写的紧急联系人电话,虽然也停用了,但后台还能查到注册信息——实名认证是个叫王德海的人,住在城北老工业区一栋快拆迁的老家属楼里。
我顺着这条线查下去,调出王德海的社保记录,现他名下注册过一家小型机电维修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弱电安装和ups电源维护,去年年底注销了。再往前翻,这家公司中标过两个政府项目的附属工程,其中一个,竟是市科技局下属实验室的电路改造。
我心里猛地一紧。
那个实验室……正是两年前k-原型机转运前的临时存放点。
k系列是我们国家自主研的高保密级量子通信模块,主要用于军用加密传输。k-虽然被淘汰了,但核心算法仍有研究价值,一旦泄露,可能影响部分旧版军事通讯安全。而更让人担心的是,最新的k-正处于测试阶段,理论上应该是完全离网、无法远程操控的状态。
可就在三天前,我们在一次例行扫描中捕捉到一次异常唤醒信号——持续秒,来自未知节点,频率特征和k-的自检协议高度吻合。
我把这条线索标红,正准备整理报告,手机响了。赵勇来一条语音。
“问到了。”他的声音低沉,“有个老保安记得,那天早上六点多,看见一个人推着个带轮子的金属箱往c栋走。穿灰夹克,走路有点跛,右腿不太利索。没登记,也没说话,他就觉得奇怪,多看了两眼。”
我立刻打开省内技术人员伤残档案库,筛选近三年内右腿受过伤、从事过高危设备运输或维护工作的工程师。条件一设,跳出二十多个名字。我一个个比对体态和行动特征,结合园区模糊的监控画面,最后锁定五个人。
其中一人,名字跳进眼里——周临舟。
简历显示,他曾任职于某军工研究所,负责量子加密模块的测试与销毁。oo年项目终止时,他签出了三台待毁模块,回收记录只交回两台。第三台,系统备注写着“运输途中损毁”。
可问题是,所谓的“损毁”根本没有现场照片、事故报告或第三方鉴定,只有一份他本人提交的手写说明。当时机构改革,监管混乱,这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