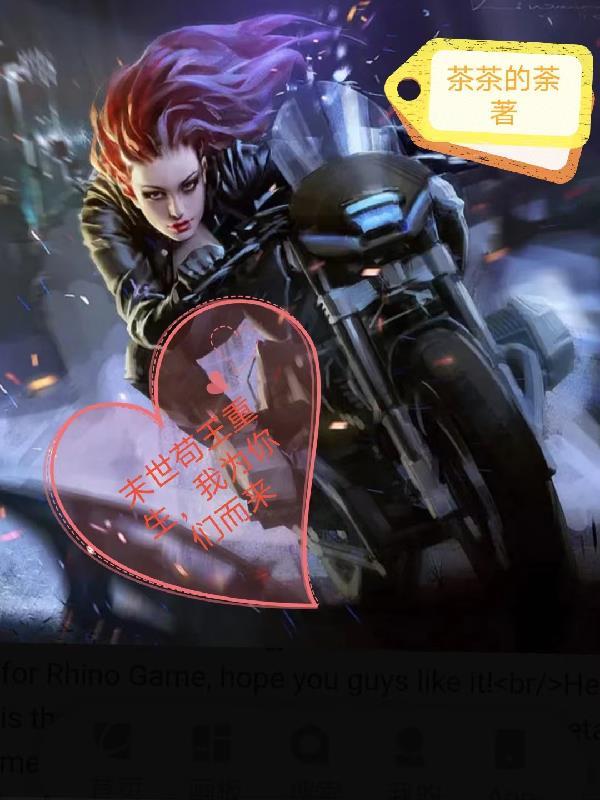我去读小说>锦棠深绣 > 第110章 惊变(第2页)
第110章 惊变(第2页)
衙役用木栅栏封住了所有街口,栅栏外守着持刀的士兵,面色冷硬,不许任何人进出。栅栏内,百姓们挤在街巷里,有的哭,有的骂,有的茫然地站着,看着那些不断被抬往临时医馆的患病者。空气里弥漫着呕吐物的酸臭味,还有石灰撒放后刺鼻的碱味,混在一起,让人作呕。
临时医馆设在码头仓库里,原本堆货的地方清空,铺上草席,草席上躺满了人。症状轻重不一,轻的还能呻吟,重的已经昏迷不醒,皮肤上的红疹连成大片,像被开水烫过。医馆里只有五六个大夫,忙得脚不沾地,可病人还在不断增加,呻吟声、咳嗽声、呕吐声响成一片,像人间地狱。
老医官张景和蹲在一个重症患者身边,花白的眉毛紧紧拧着。他穿着陈旧的官服,官服洗得白,袖口磨出了毛边,可穿得整齐,连风纪扣都扣得严实。手指搭在患者腕脉上,停留了许久,又翻开患者的眼皮看了看,最后用银针挑破一个疹子,凑到鼻端闻了闻。
他的脸色渐渐变了。
不是惊惶,是某种深沉的、混杂了回忆和警觉的凝重。他直起身,对身边一个年轻医官低声说了几句,年轻医官点头,匆匆向医馆外跑去。
半柱香后,年轻医官带着云织赶来了。
云织已经换上了特制的防护服,布料是浸过药汁的粗麻,脸上蒙着多层纱布,只露出一双眼睛。她走到张景和身边,蹲下身,查看那个患者。
“张老,您现了什么?”
张景和没有说话,只是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布包,布包里是一本薄薄的册子,册页泛黄,边缘被虫蛀出细密的孔洞。他翻开其中一页,指给云织看。
页上记录的是一个病例,时间是“永昌元年三月”,地点“杭州城西码头”,症状“突高热,呕吐,身起红疹,三日毙”。旁边有批注,字迹工整:“疑为人投毒,毒源不明,后未再。”
“二十年前,我还在府衙医馆当差。”张景和的声音嘶哑低沉,像陈年的木头摩擦,“那时杭州城也爆过类似的病,症状一模一样,死了三十七人。我们查了很久,最后在一口公井里现了异常——井水颜色不对,有异味。取水样查验,里面掺了东西,不是寻常毒药,是一种混合了多种药材和矿物的奇毒。”
云织的眼睛亮了起来:“毒源查到了吗?”
“没有。”张景和摇头,花白的头在昏暗的光线里像一团蓬松的棉絮,“当时抓了几个嫌疑人,可都咬死了不认,后来陆续‘病故’在牢里,线索就断了。那场病来得快去得也快,井水换过之后,再没爆过。我们都以为是偶然。”
他顿了顿,看向医馆里那些痛苦呻吟的患者,眼神里有一种历经沧桑后的悲悯:“现在看来,不是偶然。”
就在这时,阿青匆匆进来。他手里捧着几个瓷瓶,瓶口用蜡封着,瓶身贴着标签,写着取水的位置。
“大人,”他对云织说,“三口公井都查了,西街口那口井的水,颜色浑,有怪味。这是水样。”
云织接过瓷瓶,拔开蜡封,凑到鼻端闻了闻。水的气味很淡,可仔细闻,能嗅到一丝若有若无的甜腥,像腐败的桂花混着铁锈。她取出一根银针探入水中,银针没有变黑——不是寻常的砒霜类毒药。
她又取出一张特制的试纸,浸入水中。试纸迅变色,不是单一的色,是从边缘开始,慢慢晕染出青、紫、红三色交织的诡异图案,像某种扭曲的花纹。
“三色毒”张景和倒吸一口冷气,“和二十年前那口井里的毒,一模一样!”
云织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她将试纸小心收起,看向阿青:“井边可有现?”
“有。”阿青从怀中取出一小块布片,布片是深灰色的,边缘被撕扯得不整齐,上面沾着暗褐色的粉末,“在井台缝隙里找到的,粉末还没完全化开,应该是最近才撒进去的。”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云织接过布片,用银针挑起一点粉末,放在鼻端闻了闻,又用舌尖极轻地碰了一下——只碰了一下,立刻吐掉,用清水漱口。她的脸色凝重起来:
“这粉末和从谢将军伤口取出的碎木上沾的火药,气味相似。里面都有海外才有的矿物成分。”
医馆里一时寂静。
只有患者的呻吟声,远处百姓的哭喊声,还有仓库外风吹过篷布的哗啦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却更衬出这一刻死一般的寂静——那是一种被巨大阴谋笼罩后,毛骨悚然的寂静。
苏绣棠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所以,不是天灾,是人祸。”
她不知何时来了,站在医馆门口,素白的常服在昏暗的光线里像一抹冷月。脸上没有惊惶,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沉到极致的冷静,冷静得像深冬的冰湖,表面平静,底下却涌动着暗流。
“白莲组织的余孽,趁海战后混乱,在城西水井投毒,制造恐慌。”她走进医馆,脚步声很轻,却每一步都踏在人心上,“目的呢?拖住我们,为逃脱的那四艘敌舰争取时间?还是另有图谋?”
没有人能回答。
张景和缓缓站起身,向苏绣棠躬身行礼:“大人,当务之急是解毒。二十年前那场毒,我们最后是用‘龙涎香’为主药,配以七味草药,熬成汤剂,才救回部分患者。可龙涎香是海外才有的稀罕物,价比黄金,杭州城库存恐怕不足。”
“龙涎香”云织喃喃重复,眼睛忽然一亮,“睿亲王的旗舰上,可能配有!”
苏绣棠看向阿青。阿青立刻道:“沉船打捞还在继续,但船体破碎严重,搜寻需要时间。”
“没时间了。”苏绣棠走到一个重症患者身边,蹲下身,看着那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看着那布满红疹的皮肤,看着那微弱起伏的胸膛。她的手指在袖中收紧,指甲掐进掌心,刺痛让她保持清醒。
她站起身,声音不大,却让整个医馆都安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