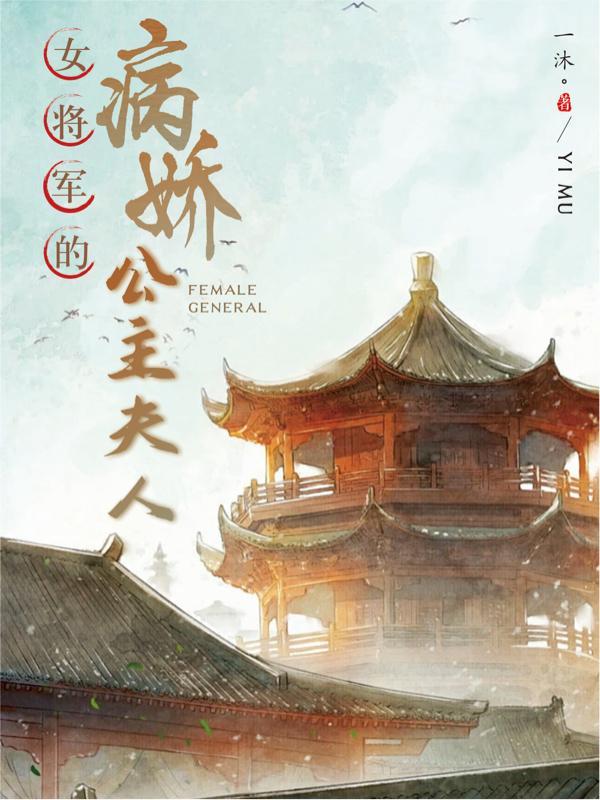我去读小说>毒酒一杯家万里 > 110120(第21页)
110120(第21页)
宋饮冰和韩渐皆站住了脚步,正想折返,忽见后面的人群被一女子奋力地拨开,推搡时自有人呵骂,“这人谁啊,挤什么劲儿……”
宋饮冰道:“悯姑娘……是悯姑娘。”
韩渐闻言,忙同宋饮冰一道上前,伸手替张悯分道。
“都往后退几步,让条道出来……都退几步,给张悯姑娘让条道出来!”
人群推搡,张悯病体难行,几度跌倒,好在李寒舟远远地看清了张悯的脸,立即令道:“去把张悯姑娘带过来。”
镇抚司下来,人群很快被劈开了一条空道,张悯在空道之中站住,许颂年的身体,就在三丈之外。他身上只有一件白色的底衣,却异常地宽大,根本不合体。杜灵若跪坐在许颂年的身边,哭得如同泪人,声音也断断续续地:“掌印死前叮嘱我,一定要等到阿悯姐姐来,阿悯姐姐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用,我护不好掌印的身子……我没用啊……”
张悯有些恍惚,身子一歪,险些栽倒。
宋饮冰见此忙要上来扶她,却被张悯避开,她重复着杜灵若的话,“一定要等到我来……一定要等到我来……”
一面说一面掐起虎口,强压下满腔悲意,令自己冷静,一步一步地朝那具破烂的身体走去。
三丈之远,她竟不知走了好久,近前时,血腥味充斥了她的鼻腔。
李寒舟在旁道:“张悯姑娘,陛下恩准,你替罪人收尸。此人你可带回,但不能买棺装椁,也……不能发丧。”
“好……我明白。”
她说着,在尸体前缓缓地蹲下身,抬起那只沾染着乞丐浓痰的手,掏出怀中绢帕,仔细替他擦去,哽咽道:“我想理一理他的身子,你们可以背过身去,避一避吗?”
李寒舟点了点头,抬头道:“都转身,往后退。”
人群被镇抚司压着朝后退去,张悯这才放下许颂年的手,她深吸了一口气,逼自己稳住摇摇欲坠的身子,颤颤地伸出一只手,撩开了许颂年的衣襟。
那破碎的血肉顿时逼入她眼中,奇怪的是,她平时连荤腥多了都觉得恶心,可面对这一滩血肉,她却一点都不想吐。
这么多年,虽不在一处耳鬓厮磨,但这世上至亲至疏夫妻说得最是精妙,他们一直都有默契。
张悯明白,许颂年绝不忍心让她看见他此时的模样,除非,他要用他自己的尸体,告诉她什么。
果然,她在衣襟之内,看到了一封以血为墨,写给她的信。
“卿莫怪,狱中不得纸笔传书,隧潦草相别。吾因私盗内藏,天子定颂年死期于今日,只堪先落款在尾,若卿不见结语,便是颂年命绝此时,不及交代。”
“卿且记,卿志亦我志。”
“本愿承张氏之宗,奉吾妻百年。”
“知不可乎再得,托遗响于悲风。”
张悯读至此处,天上高风由上卷下,朝着她扑来,吹起她病中未挽的长发,拂过那张了无生气的脸庞。
那是张悯少时所爱的《赤壁赋》,他日是“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而今终再不可得。
“知不可乎再得,托遗响于悲风……”
张悯呢喃着,忍泪将衣襟彻底翻接,后面的文字明显更加潦草凌乱,似是死期将至,无常催发,也似他临死恐惧,终至不可控笔。
“卿莫忘,秋冬养身,春夏提笔。吾终生仰羡卿之文墨,愿临死长记,亡前再誊。”
其后文字,几乎是为了抢时,乱如蓬草,但张悯认得,他命绝之前的最后一刻,写的是那篇满城流传的舞弊之文,是她的文章。
“人处世若失公正,犹夜行无烛,终坠渊薮矣。”
“人处世若失公正,犹夜行无烛,终坠渊薮矣。”
“人处世若失公正,犹夜行无烛,终坠渊薮矣。”
“人处世若失公正,犹夜行无烛,终坠……”
最后一遍,字迹已乱得难以分辨出字形,终究未能写完,果然是“若不见结语,便是颂年命绝此时,不及交代。”
而那落款之处,离之结尾甚远,又果然是他提前写好,要她慎看再看。
张悯揉了揉有些模糊的眼睛,倾身看去,但落款见自字迹比前面都要公整,文字如下:
四月二十七日于高墙火场
永继卿志
永护卿愿
张悯忍着心中无限悲意,细审最后的落款。
“高墙火场,用继我志,永护我愿……为什么是高墙火场?高墙……庆阳高墙,火场……”
她想着,忍悲再读前文。
“吾因私盗内藏,天子定吾死妻于今日…”
私盗内藏…
张悯至此猛然明白了许颂年的死因,她再度朝那日期看去,“四月二十七日……杜灵若。”
杜灵若忙回身道:“什么?”
张悯猛将衣襟覆上,转身道:“今夕何日?”
“四月二十……二十六日啊……”
张悯手指一握,轻道:“明日,庆阳高墙火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