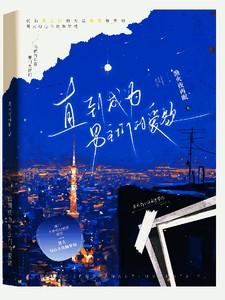我去读小说>责天纪 > 第289章 人间烟火气(第1页)
第289章 人间烟火气(第1页)
老人紧紧攥着居民塞来的帕子,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帕子的粗糙纤维蹭着手背的伤口,疼得他微微蹙眉。
他望着何嘉琪狼狈逃窜的背影,又猛地转头看向陆云许,浑浊的眼眶瞬间泛红,带着后怕与感激,声音颤巍巍的:
“后生,你可闯大祸了……何守将在镇上一手遮天,势力大得很,你快些走,往郢城方向躲躲,晚了就来不及了!”
陆云许却只是缓缓蹲下身,动作因右腿的麻痹带着些许滞涩,指尖小心翼翼地捡起地上还能复用的竹条,拂去上面的尘土,声音平静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老人家,我不走。他若敢再来,我便再教他一次怎么做人。”
淡金色的阳光落在他破烂的黑袍上,虽满身伤痕,却像一株扎根大地的青松,透着一股让人莫名安心的力量,瞬间压下了老人心头的惶恐。
何嘉琪带着随从灰溜溜跑远后,市集上紧绷的气氛如同被戳破的气球,瞬间松弛下来。
原本躲在角落的居民纷纷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刚才的场面,语气里满是压抑许久的解气。
“打得好!这何小崽子早就该有人治治了!”
“后生胆子真大,可算替咱们出了口恶气!”
卖竹篮的老人顾不上收拾地上的断竹条,一把拉过陆云许的手腕,掌心裹着常年编竹篮磨出的厚茧,粗糙却带着滚烫的暖意。
他另一只手从怀里掏出个叠得方方正正的粗布包,布包边角磨得白,针脚处还缝补过好几回,显然用了许多年。
打开布包,里面是晒干的草药,叶片蜷缩着,带着淡淡的苦味,还混着几株开着小白花的薄荷,清新的气息冲淡了些许血腥味——
那是用来镇痛消肿的。
“后生,快拿着!”
老人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哽咽,手背上的伤口还在缓缓渗血,他却浑然不觉,只顾着把草药往陆云许手里塞。
“这是我老婆子生前晒的治跌打损伤的药,你刚才跟他们动手,肯定也碰着了,回去用温水泡开敷在伤处,能止疼。”
怕他不肯收,又急忙补充道:
“这药不值钱,后山遍地都是,你可别嫌弃。”
旁边卖粥的妇人也端着个粗瓷碗,费劲地从人群里挤了过来,碗里盛着温热的小米粥,上面卧着个金黄的荷包蛋,油花在阳光下泛着细碎的光,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
“后生,刚看你脸色苍白得很,快喝碗粥垫垫肚子,打架最耗力气了。”
她身后跟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手里攥着个热乎乎的麦饼,小脸憋得红扑扑的,踮着脚尖努力把麦饼往陆云许面前递:
“大哥哥,这个给你,我娘做的,可香了!”
之前想扶老人的那个妇人,手里提着针线筐也挤到前面,一把拉住陆云许破烂的黑袍下摆,指尖轻轻摩挲着撕裂的边缘,眼里满是心疼。
“后生,你这袍子破得厉害,风一吹肯定凉,我给你缝两针吧?”
她不等陆云许回答,就从筐里掏出一团青灰色的线,麻利地穿针引线,指尖翻飞间,细密的针脚已经落在了破口处,动作又快又稳,显然是常年做针线活的巧手。
“虽说线色不搭,可至少能遮风挡雨。”
市集上的烟火气重新升腾起来,夹杂着草药的微苦、米粥的醇香、麦饼的麦香,还有居民们真切的关切,像一股暖流,缓缓淌进陆云许的心底,冲淡了身处异乡的茫然与孤寂。
他望着眼前这些淳朴的面孔,握着掌心温热的草药,忽然觉得,哪怕此刻修为被封、归途难寻,这份人间暖意,也足以支撑他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继续走下去。
陆云许双手捧着怀里的东西,指尖次第触到粗布包的粗糙温热、瓷碗的温润暖意,还有小姑娘递来的麦饼残留的体温——
那温度像是带着生命的韧劲,顺着指尖一点点蔓延开来,轻轻裹住他的心脏。
之前因丹田被封、身处异乡的茫然与孤寂,如同被春日暖阳融化的冰雪,瞬间被这股纯粹的淳朴善意冲散,连经脉里的钝痛都仿佛淡了几分。
他低头看着掌心的草药,干枯的叶片蜷缩着,却透着倔强的韧性,像极了这些在底层艰难挣扎,却依旧保留着赤诚善良的百姓。
鼻尖萦绕着草药的微苦、小米粥的醇香,还有麦饼的清甜,几种味道交织在一起,竟让他眼眶莫名热。
在中三天,他见惯了修士间的生死厮杀、浊力的阴邪侵蚀,尔虞我诈是常态,从未想过,在这个没有灵力、没有修行者的陌生凡尘,能感受到如此不带半分功利的温暖,纯粹得像未经雕琢的璞玉。
“多谢各位……”
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将粥碗小心翼翼地放在旁边的石阶上,先接过妇人手里的针线,指尖触到线团的柔软,语气诚恳。
“麻烦您了,不用太讲究,能蔽体挡风就行。”
妇人笑着应下,指尖翻飞间,青灰色的线在破烂的黑袍上穿梭,针脚细密而规整,透着常年操持家务的利落。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等她专注地缝补起衣袍,陆云许才抬眼看向围在身边的居民,眉头微蹙,犹豫了片刻,终究还是开口问道:
“各位,我之前赶路时受了伤,现在浑身没力气,想问问……你们知道有什么地方,能让人恢复‘力气’的吗?”
他刻意避开了“修为”“灵力”这类字眼,只说“力气”,怕这些凡尘百姓听不懂,反而徒增困惑。
居民们闻言,纷纷停下手里的动作,面面相觑起来——
有人挠着后脑勺冥思苦想,有人凑到身边人耳边小声嘀咕,连缝补衣袍的妇人都停下了针线,皱着眉细细思索,市集上一时只剩下细碎的议论声。
过了一会儿,人群里一个拄着拐杖的老者缓缓走了出来。
老者头全白,像落了层霜雪,脸上的皱纹深深刻在皮肉里,仿佛能夹进米粒,手里的枣木拐杖顶端包着块磨得亮的铜皮,每走一步都出“笃笃”的轻响。
他轻轻咳嗽了两声,清了清嗓子,才缓缓开口,声音带着岁月沉淀的沙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