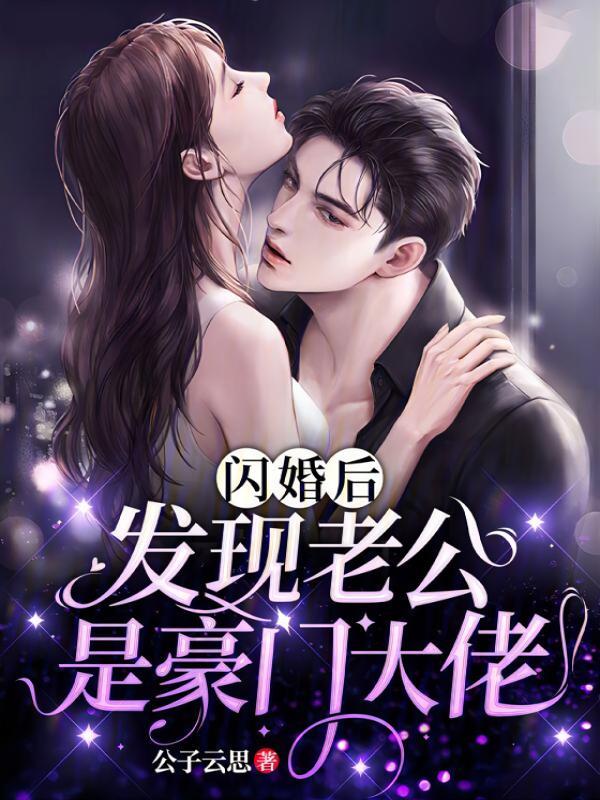我去读小说>二十一世纪庶女生存指南 > 61 遇到爱情表演艺术家也只能受伤(第2页)
61 遇到爱情表演艺术家也只能受伤(第2页)
王主任当年在学校是个草包,唯一的优点就是能跪着听话,一路混到另一家私立中医骨科的主任,就再也升不上去。没想到现在要骑到自己头上——至少是平起平坐的关系,不然不用惊动杜清和朱长跃出马。
但他想不通,自己是哪里做了出格的事,露了马脚?後续该何去何从?
杜润只觉得越想越怕,手表发出心动过速的警报。
他站在冬夜中,大口呼吸,让冷风灌进肺里,让大脑暂停运转。
他想,一会儿回到家,也许真的需要泡进浴缸里。
一夜无眠。
第二天清早,杜润还没想好如何和张束告假,张束就来敲门。对不起,今天要放鸽子了。
杜润装得委屈,张老师什麽安排?
和贝贝逛街,还能是什麽安排。晚上有时间可以一起吃饭。
杜润答了好,晚上离他还太漫长,他要先把该查的事查明白。
张束看出他的心不在焉,也不多问。等杜润的车驶离地库,朱贝贝载着张束也出发了。
“姐,一会儿在哪儿把你放下?”
张束想了想,“杜润医院的工地。”
姐妹俩还是第一次来这边,好大一片围栏,开车转了五分钟才找到入口。朱贝贝问张束要不要自己陪,张束让她去忙,这事人多不好办。而且朱贝贝太美太扎眼,一定会引人注意。
朱贝贝问她要怎麽混进工地,张束笑说先试试,等成功了,回家再给你讲。
张束让贝贝将车停远一点,停在人流大的路口。从奔驰上下来,张束多走了几步,立刻混进人群中。
进工地?不可能的。长隆的工地最规范,工长刷卡,工人出示身份牌。昨晚规划时,贝贝没有这方面经验,问张束能不能说自己是记者或者集团管事的,她说不定能弄到长隆的工作卡。张束摇头,这个工地现在出了问题,最不欢迎的就是记者和集团的人,前者乱棍打出来,後者问不到一点有用信息。
张束没过马路,一直在街对面晃。她知道再过一会儿,午休时间,工人们会鱼贯而出出来吃饭,这边有许多平价甚至廉价的摊位。她第一篇短篇小说就写了建筑工人,当年特地去采过风,没想到用在了今天。
果然,半小时後,她身旁的炒粉店坐满了戴黄帽子的工人。
张束趁乱在门口看了一圈,走进去,快速挑了个座位坐下。身边是一位上了年纪的阿姨,看上去和周君差不多,但张束知道,她的实际年龄应该比周君年轻十岁左右。在工地上讨生活的女人,皮肤老化得比一般人快很多。张束还知道,想问话丶套话,一定要找阿姨下手。甚至不用问,她们也能讲出些故事。
“阿姨,没人坐吧这里。”
阿姨摇头,同意t她一起拼桌,“没见过你呀。”
“来这边办事,随便吃一口。”
菜上来,张束点了两个带肉的,示意阿姨吃。阿姨不好意思,夹了两筷子,和身边的工友们打开话匣。
阿姨是和老公一起来的,还带着闺女儿子,一家四口都在这个工地上。当初来是听说这里钱多,没想到才开始就拖欠工资。
“在北京还敢欠薪?”张束装作惊讶,“那大家一起闹呀,集体罢工。”
闹不起来,阿姨说,这家老板好精明,拖欠工资也不是一起拖,今天欠这组,明天欠那组,大家都是分工种分组闹,起不了规模。有天夜里闹得凶了,第二天钱就填了进来,而闹的那批人也一个个不见,总是往里进新的。
总之,医院的工期慢于预期,和计划表上的安排不太对得上。
张束去结账时听到阿姨的丈夫用家乡话骂她。丈夫比阿姨警惕,让阿姨少说话。阿姨说张束看着像个好女娃,男人说新闻上的那些暗访都是这些个好女娃做的。再说这种事,哪个工地没有,都一样,钱进了口袋就得了。
张束想了想,替阿姨一家买了单。
确实不新鲜,但张束总觉得哪里不对。她给杜润发了条微信,问他在不在公司,杜润没回。
杜润此时正坐在一家小四合院改的茶室里,环境谈不上雅致,有点粗糙。他提前几小时就到了,转了一圈,发现包间毫无隔音效果。里面人说什麽,外面听得一清二楚。他好奇问老板,这是什麽神秘地方,连个名字也没有?老板是老北京,一个劲搓手解释,岁数大了,不会弄网上的那些东西,这家茶馆就叫“茶馆”,开了挺久,都是老客,这周边一家医院,人来人往的,平时也不缺生意。
杜润笑自己想得太多,把生活想成谍战,把父亲和朱长跃想成敌人。哪儿那麽复杂呢。自己根本不配成为人家的对手。
选在这个地方,不过是离王主任所在的分院近,没人怕杜润知道。
到了十一点半,人才姗姗来迟。杜润从门缝往外看,三张熟脸在门口寒暄握手,王主任的腰都快弯到了地上。
“朱总丶杜总,久仰二位大名,喊我小王就行。”
杜清笑得爽朗,“过谦。以後就是我们医院的王院了。”
朱长跃也笑着伸手,“王院,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