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读小说>灶神的味觉:庶女厨娘逆袭录 > 第389章 死讯再现暗局初成(第1页)
第389章 死讯再现暗局初成(第1页)
苏小棠的指尖刚触到纸条,湿黏的温热便顺着指腹爬上来。
那是血,还带着未散的腥甜,像刚从活物血管里渗出来的。
她喉间紧,后颈那枚淡红色的印记突然烫得惊人,仿佛有团火在皮下乱窜,烧得她眼前泛起金星。
"啪嗒。"青瓷茶盏砸在青砖地上,碎成几瓣,惊得烛火猛地一跳。
苏小棠踉跄着扶住桌角,借着晃动的光看清纸条上的字——"别去,她已经死了第二次",墨迹在月光下泛着乌青,最后一个"次"字拖得老长,像是笔尖突然被外力撞偏。
窗外的竹影突然剧烈晃动。
她咬着唇推开窗,夜风冷得刺脸,窗台上只余半枚火纹印记,与三个月前刺杀她的赤袍人腰间玉佩的纹路分毫不差。
远处屋顶尽头有道黑影闪过,身形瘦削如竹枝,足尖点瓦的声音轻得像鸟振翅,显然是个惯使轻身功夫的好手。
"他们想让我害怕。"苏小棠攥紧纸条,指节白。
后颈的灼痛渐渐退成钝痒,她盯着黑影消失的方向,眼底却漫上冷意——怕?
她十二岁被嫡姐推下井时没怕,十六岁替母顶罪挨三十鞭时没怕,现在更不会。
"小棠。"
身后传来熟悉的沉哑嗓音。
苏小棠回头,就见陆明渊立在门口,月白锦袍被夜风吹得翻卷,腰间玉牌泛着幽光。
他手里还端着盏温茶,显然是听见动静从隔壁过来的。
"给我。"他伸出手,指尖沾着未干的墨渍——定是方才在隔壁批折子。
苏小棠把纸条递过去,看着他眼尾微挑,指腹摩挲过血渍:"血是新的,墨迹未完全渗纸。"他抬眼时,眼底寒得像结了冰,"恐吓,也是试探。"
"怕什么?"
陈阿四的大嗓门突然炸响。
苏小棠转头,就见御膳房掌事踩着满地瓷片冲进来,腰间短刀出鞘半寸,刀身映着他涨红的脸:"咱们现在连灶神都关进去了,还怕几个跳梁小丑?"他拍着胸脯,粗布围裙上还沾着白天和面的面粉,"我现在就追过去,把那孙子揪下来!"
"阿四!"苏小棠跨前一步,按住他手腕。
陈阿四的腕骨硬得硌手,短刀出鞘的"铮"声在屋里回荡。
她能感觉到他掌心的温度——是常年握锅铲练出的厚茧,此刻正因为激动微微颤。"他们故意留纸条,就是要引我们追出去。"她压低声音,"天膳阁的暗桩分布、咱们的人手底细,全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曝了光。"
陈阿四的短刀"当啷"落回刀鞘。
他瞪着眼睛张了张嘴,最后"哼"了一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震得桌上账册哗啦乱响:"那总不能干等着挨刀吧?"
"自然不。"陆明渊将纸条折成小方块,收进袖中。
他转身时,袖口露出半截玄色里衬——那是他最爱的素色暗纹,却在今夜多了几分冷硬,"先查这血的来路。"他看向苏小棠,目光软了些,"你后颈的印记又烫了?"
苏小棠摸了摸后颈,那里的皮肤还带着余温。
她想起老厨头临终前的话,想起账册上混着两种笔锋的朱砂线,喉间突然紧。
她转身从柜中取出个檀木匣,掀开时,《灶神录》残页特有的霉味混着檀香涌出来。
"三重试炼。"她翻到某一页,指节抵在泛黄的纸页上。
残页边缘有老厨头用朱笔批注的小字,"失亲、失信、失己。"她念出声时,声音轻得像叹息。
三个月前母亲的血沫,上个月老厨头冰凉的手,此刻都在眼前晃——原来"失亲"早就在她十四岁那年应验了。
"他们是在逼我面对过去。"苏小棠合上残页,指尖压在"失己"两个字上。
烛火在她眼底跳了跳,照出她紧绷的下颌线,"可我偏要让他们知道,苏小棠的过去,由不得别人指手画脚。"
陆明渊走过来,手掌覆在她手背。
他的掌心带着常年握笔的薄茧,温度正好:"需要我做什么?"
"明天。"苏小棠抬头,目光扫过窗外渐亮的天色,"天一亮,封锁天膳阁所有出口。"她的声音沉下来,像压着块烧红的炭,"再让厨房的老伙计们布个五感迷阵——既然他们想玩心理战,那便让他们先尝尝自己设的局。"
陈阿四突然笑了,露出两排白牙:"这才是我认识的苏掌事!"他抄起桌上的残页翻了翻,又"啪"地拍回去,"我这就去叫人磨香料,迷阵的花椒要选蜀地的,桂皮得用三年陈的"
他的声音随着脚步声渐远。
陆明渊替苏小棠理了理被风吹乱的鬓,低声道:"我让人去查青焰山的线索。"他顿了顿,"还有,后颈的印记若再烫"
"我知道。"苏小棠打断他,指尖轻轻碰了碰他的手背。
窗外的天已泛起鱼肚白,她望着东方渐亮的晨光,眼底的冷意慢慢凝成一团火——这一局,她等了太久。
晨雾未散时,天膳阁的朱漆大门"吱呀"闭合。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苏小棠站在廊下,看四个精壮伙计将铜锁扣进门槛的暗槽——这是她昨夜与陆明渊反复推敲出的三重封锁:明锁封门,暗桩守墙,更有三拨厨子扮作送菜人在巷口游荡,专等那些想探消息的人撞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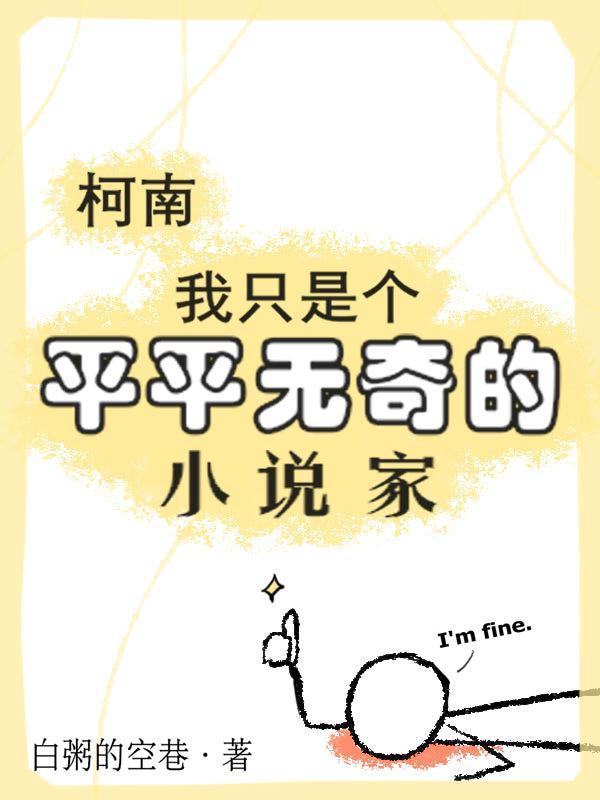
![(排球同人)[排球少年]猫猫男友他太会+番外](/img/23186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