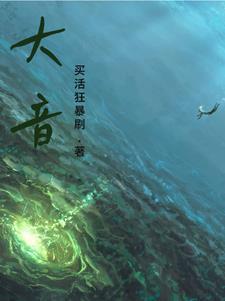我去读小说>港岛有雪 > 第163章(第1页)
第163章(第1页)
沈郁澜咬着烟,全身都因为闻砚书抚摸脸颊的动作而颤栗不止,却没有让这支烟掉落,因为落点一定是闻砚书的手臂,这支正燃的烟,会烫到她。
还记得那晚,沈郁澜背对闻砚书跪在床上,和她发出害羞的请求——可不可以让我咬一支烟。
十分钟,要是这支烟没落,闻砚书就得让她一次。
可惜她连五分钟都没有坚持住,腿根抖个不停,边颤边哭地求闻砚书停下来,不要再欺负她了。
和现在一样。
只不过,那晚那支烟,沈郁澜没有咬住。但这一支,她死死咬住了。
要么,她是心疼怕会烫到闻砚书。
要么,她是对闻砚书暗示性十足的抚摸动作没有反应了。
闻砚书开始不淡定了。
她不相信沈郁澜会变心这么快,心不向着她,难道连身体也不向着她了吗?
外面都是行人,常有人往车里面张望一眼,即使外面看不见里面,还是会有一种被窥视的不安全感。
可闻砚书压不下去的手接下来去做的事有点疯狂,她扯下系在腰间的装饰皮带,在沈郁澜恐惧的注视中,动作偏执地把她双手背到身后捆住了。
“唔……”
双手不能动弹,嘴里咬着烟说不出话,呜咽声抗拒声还有因为闻砚书的抚摸逗弄像是太舒服了而喘出来的声音全部闷在喉间,只有一双流泪到楚楚可怜的眼能够诉说情绪。
这般暴虐地把她掌控在手心,她不会再去奔向谁了,谁也不会来把她抢走了。
闻砚书双眼露出前所未有的兴奋光芒,手指缠绕住她的一缕头发,笑说:“bb,今晚,我们再玩一遍咬烟的游戏,好不好?”
钢笔是用来写字的
车门打开。
沈郁澜下车那一瞬,又僵又软的腿差点没支撑住身体,前后踉跄一下,她靠住车门,摸了把依然泛着潮红的脸颊。
不经意往车里面看一眼,那道带着凉意的视线压过来,腿又开始打颤。
闻砚书左手轻轻握着一支纯黑商务钢笔,右手捏着一张消毒湿巾,仔仔细细地把钢笔表面擦拭干净,细长的手指漂亮得让人移不开眼。
她没有避讳让外面的人望见她,包括那支已经被她反复消毒过的钢笔。
将要把钢笔放回笔盒,她抬起眼眸看向红透脸的沈郁澜,眼尾惯性上挑,拿在手里的钢笔转了两下,接着以一种妩媚的姿势从眉眼往下滑落到嘴唇,耐心地停留在那里,等沈郁澜偷瞄她一眼时,那支钢笔,被她轻轻咬住了。
旁人只会觉得这是一支普通的钢笔,但对于沈郁澜来说,这跟赤身裸体在大庭广众之下没有区别。
不禁又想起刚才的事。
皮带捆住手、嘴里咬着烟时,不断被勒紧的脖子让沈郁澜像渴望水的鱼一样,拼命挣扎,只是哪里都被嘴角噙着坏笑的闻砚书给束缚住了,她就像在水里扑腾的鱼儿一样,双腿不安分地张开,像是在自救。
“点头或者摇头。”闻砚书语气无温。
沈郁澜满眼畏惧地看她,把头扭向另一边,这是对咬烟的游戏没兴趣了,也是对曾经那么渴望的闻砚书没兴趣了。
“很好。”闻砚书锁住车门,随手从中央扶手箱拿起一个长条状的盒子,偏执的笑容里裹着一丝慵懒,“郁澜现在是不是不想说话呀,没关系,阿姨有的是时间……”
曼妙身体弯下去,长卷发从沈郁澜颤栗的脖颈扫过,一手牢牢控制住还在隐隐乱动的沈郁澜,一手把笔盒按在座椅打开。
各种复杂的欲望缠绕在她看向沈郁澜时销魂的眼神里,接着把话说完,“等你变乖。”
沈郁澜大力扭动身体,想要逃脱,裙摆不小心褪到腿根往上,不好意思把隐秘的部位袒露出去,她羞耻地夹紧双腿,不想让闻砚书看到。
闻砚书不紧不慢地给那支钢笔和手消毒,“郁澜,把脸转过来,看看我。”
沈郁澜不仅没有,反而把脸往那边又转了一点。
她越来越不听话了。
不听话,是要受到惩罚的。
车窗外人声嘈杂,总感觉有人正往里面看,眼尾飘红的闻砚书正在进行一次温柔的暴力,钢笔是用来写字的,当然,在任何地方写都可以,探向那里时,刚好是最舒服的力量。
沈郁澜发出哼声。
“郁澜,听话,转过来看我一眼。”
“不,不要。”沈郁澜不想烟落,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
“怎么还是不听话呢。”
闻砚书不需要低头看,也能在最适合的位置写出最好看的字,一次就够了,她偏偏一次又一次,让说不了话的沈郁澜压抑着哭起来。以前闻砚书最怕沈郁澜哭,现在看着她的眼泪,心里竟然邪恶地滋生出一种难得的欣慰和满足。
闻砚书懒懒地垂眼,看着在她怀里边满足边抗拒的沈郁澜,笑了,“郁澜不肯摇头,也不肯点头,看来是害羞了,既然这样,那这一次,规则就由我来定。如果剩下半支烟你没有咬住,烟落了,那么,今晚,换我来咬烟,怎么样?”
沈郁澜不知道有没有仔细听,眼神呆直,有种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在哪的感觉,不断闪躲然后不断被控制,终究是受不住越来越潮湿的挑逗,她哭出声音,双腿用力阻止闻砚书还想写字的动作。那一瞬,那支快要烧完的烟,落了。
闻砚书捡起掉落的烟头,把烟灭了。
“明明可以咬住,偏偏让这烟落了,看来郁澜也很期待我来咬烟,是吗?”
嘴巴总算得到解放,刚才憋着说不出来的话现在也全都可以说了,沈郁澜嘴硬道:“不可以,要是薛铭哥哥知道了,他会生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