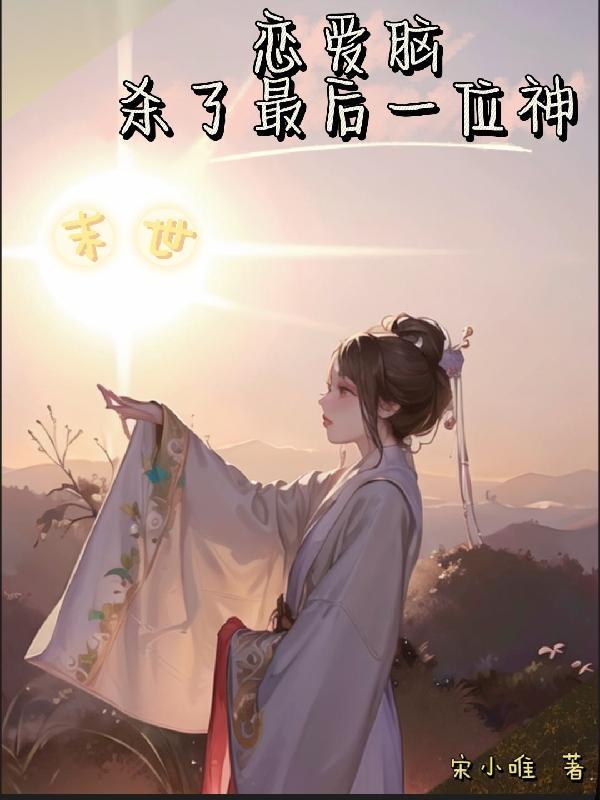我去读小说>权臣:如何防止皇帝发疯 > 第68章(第3页)
第68章(第3页)
可他脑海里,却不是这盏茶、也不是眼前这间屋。
是火、是血、是被烧过的乱葬岗。
这世上,不如人愿者,十有八九。
任玄本是不主战的,任玄主降,让皇城去降。
那个时候,他兵临太玄城下,西北的岳暗山陈兵太仓关,北方的陆行川兵指太夕城。
皇城外最后三处屏障,危如累卵,天下大势,一眼分明。
皇城中,除了卢节那老顽固,多的是‘聪明人’。
暗中送来的投效书,早早的堆满的任玄的帅案,任玄看的分明,这皇城,早晚不战而降。
在云中帅所,在秦疏面前,任玄振振有词的说着什么‘上之上者,不战而屈人之兵’,讲着什么‘一念之失,生灵涂炭。’。
其实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他是刀,秦疏指哪里,他就往哪儿砍。
他为秦疏杀人,不讲信仰,不论对错。不是忠诚,不是理想。只是效力,只是顺势。
——只是杀人而已。
可在兵临皇城的当下,任玄这把刀,有了自己的想法。
他想到了皇城中,有人为定一桩案、为论一桩罪,都要将卷宗反反复复的翻阅上几遍,字字句句的核对确认。
那才不过几条人命?
任玄不再想提刀进皇城。
他不想把自己搞得像个满手血腥的万人屠一样。
哪怕他本来就是。
他在自己心里,看到了一块还未烂透的地方。
他从没想过那东西还在。
可它就在那,冷不丁地亮了一下,他动了念头——进了皇城,他就撂挑子。
反正他有的是办法、有的是把握保下卢士安。
秦疏要杀的人,名单太长了,长到他一眼望过去,都觉得皇帝疯的厉害。
他懒得掺合了。
他怕哪天,卢士安也觉得他疯的厉害。
任玄都想好了,等入了城,他就不再帮秦疏杀人了。
到时候,就让秦疏一人去疯。
人总是惯性地,把事情往好处想。
他也是。
他以为自己还算个正常人,能笑,能说,能在刀口上把玩一句调侃。
可他不是。
他以为自己还有退路。
可他没有。
他终究,还是提着刀进了皇城。
那天风很大,天色未亮。
雨像是昨夜就开始落,沥沥不歇,落了一夜,也冷了一夜。
任玄没有走御街,没有入皇宫,亦未赴那场百官齐聚、声乐鼎沸的宫中盛宴。
毕竟,皇帝也没去。
秦疏不喜欢宴会,从前,是那陆溪云不喜欢,秦疏总要分神去照顾对方的百无聊赖。
后来,是皇帝下意识的分神时,那空无一人的角落,会让皇帝陷入极度的心烦气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