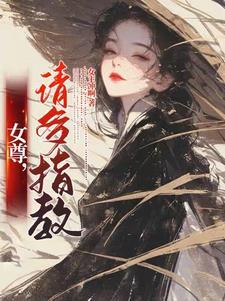我去读小说>起尘记 > 第1章 山村少年(第1页)
第1章 山村少年(第1页)
秋日傍晚,橘黄色的余晖洒在乡间土路上,将独行少年的身影拉得细长。
他叫裴炎,约莫十岁,是这裴家村里一个寻常又不那么寻常的少年。
一身洗得白的补丁旧衣,掩不住他眉眼间的清秀,尤其是那双黑亮沉静的眼睛,透着股远年龄的聪慧与沉稳。
他臂弯里挎着个半旧的柳条篮,里面装着些沾泥带土的“土果”——这是附近贫苦人家孩子能换几个铜板的稀罕物。
篮子不算满,但裴炎的脚步却有些蹒跚,额角带着细汗。他脸上没有疲惫,反而有种奇异的专注,时而兴奋,时而纠结。
他的右手,总是下意识地、小心翼翼地按在腰间一个鼓囊囊的衣袋上,仿佛那里藏着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二娃子!”
一声洪亮的吆喝打断了他的思绪。
迎面走来的是牵着大黄牛的张大叔。
汉子四十上下,皮肤黝黑,满脸风霜,是地里刨食的老把式。
“张大叔。”裴炎停下脚步,规规矩矩地应声,手指却不自觉地在衣袋处蜷紧。
“又去挖土果了?真是个好孩子。”
张大叔赞许地点点头,目光却飞快地扫过裴炎的篮子,在看到那几个格外饱满的大果子时,眉头微不可查地皱了一下,
“这十里八乡,像你这么懂事的娃可不多见。只是……”
他话锋一转,声音沉了几分:“能长出这般大果子的,也只有后山那半腰险地了吧?你今天又上那儿去了?”
裴炎微微低头,嘴角牵出一丝腼腆,算是默认。
“唉!”张大叔叹了口气,粗糙的手拍了拍牛背,“二娃子,大叔知道你想为家里分忧。
可那地方真不是闹着玩的!陡得很!去年小黑子摔断腿的事,你忘了?
一个好端端的后生,现在……说亲都难了。”
他看着裴炎沉静的小脸,嘴唇动了动,似乎想提些关于后山更玄乎的乡野忌讳,但最终只是化作一句催促:
“快回家吧,天快黑了,你娘该等急了。以后……尽量少去。”
说完,他便牵着牛,慢悠悠地走了。
裴炎站在原地,看着张大叔宽厚的背影消失在暮色里。
他听出了那未尽之意,但此刻,他所有的心思都被衣袋里那件意外得来的东西占据了。
那东西像块温热的炭,熨帖着皮肤,也灼烧着他的好奇心。
他加快脚步,朝着村头那缕熟悉的炊烟走去。
“二娃,回来了!”院门吱呀一声从里推开,裴母快步迎上,接过沉甸甸的篮子,心疼地低语,
“以后可不敢再去后山了,太险了,咱宁可少这几个钱……”
“娘,我饿了。”裴炎抬起脸,用带着点童稚的声音岔开话题。这招屡试不爽。
果然,裴母立刻打住话头:“饿了吧?灶上温着半个窝头,先垫垫。
你爹和你哥去镇上了,等他们回来就开饭。”
“爹和哥去镇上做什么?”裴炎接过窝头,咬了一口问道。
裴母一边收拾灶台,一边心不在焉地答:
“还不是为你哥去木匠铺当学徒的事。按理说早该回了……”
她的声音里透着一丝紧张,目光不时瞟向院外昏暗的小路。
裴炎没再问,默默吃着粗糙却实在的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