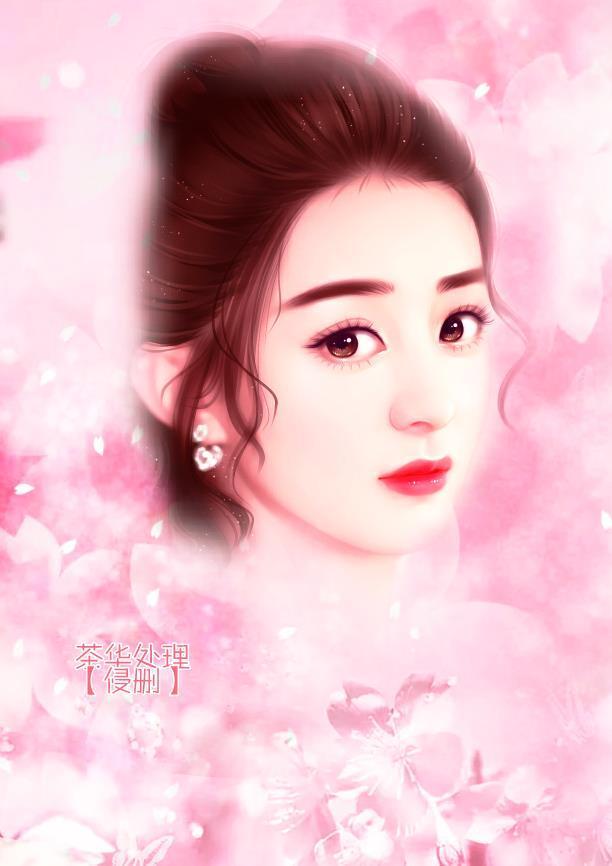我去读小说>观云三百年 > 第227章 出尔反尔不折手段(第3页)
第227章 出尔反尔不折手段(第3页)
诸人扭头来看他,姚圣珊就差一脚踹过去,碍于文人礼数,终只是嫌弃的瞪了一眼。
破布迎难而上,扯了扯谢徴的衣摆:“你别怕了年轻人。”
太乌在不算很远的地方被挂在柱子上,四周干干净净的没有一丝机关布置的痕迹,只有一个提刀的人站在他的背后露出影子,随时准备终结一条不屈的生命。
破布的话起不到任何作用,姚圣珊眼神的反对也微乎其微,翟巡翟玩对昆仑奴的轻视则更像是一剂良药,灌的谢徴内心苦涩,往事历历,叫他不敢朝前走。
于是谢徴挥手止兵,朝后退了半步,再转身,驱马径直回了大军营帐。
因了突然的撤兵,十九州兵马驻扎在中州城外的日子又多了一天,所有人内心都被一股躁动的火烧的格外不安,但因谢徴是一座冷峰,火还烧不起来。
翟巡和翟玩道:“关照拦不住的道,竟被昆仑奴拦住了。”
大部分人不会懂谢徴为何因为一个区区昆仑奴而止住脚步,也不懂他在营帐内都在想些什么。
直到天亮时,姚圣珊在谢徴的帐内瞌睡,被一声号令吵的魂飞天际。
“报——皇宫已围!待储上下令即刻进攻!”
“什么?”
姚圣珊一个激灵,睁眼看见对面的谢徴双眸禁闭,还是打坐的模样。
“储上!”姚圣珊听见自己的舌头在打结,“储上的命令吗?”
谢徴睁眼,将拂尘从左手甩荡到右手,平静地回复:“圣珊,随我去接太乌。”
姚圣珊于是一路小跑跟在谢徴后面,在营帐扎寨的青草地上弯弯绕绕,在天色蒙蒙亮的蓝霞之下,看见了被兵卒簇拥抬入军营的一幅骨头架子。
骨头架子名叫太乌。
谢徴握住太乌那只茧子比皮肉还厚的手,叫他名字,眼睛没有泪水,尽是胜券在握和相逢的喜悦,不住地道:“太乌!你好不好?太乌,你饿不饿?太乌,你累不累?”
姚圣珊看见那太乌响了一声,像春日柳树底下勉力破土的蚕蛹,他尽力一听,听见两个字——表哥。
蚕蛹蛄蛹,姚圣珊又听见几个字——我要死了。
太乌累的要死一样,昏昏沉沉的睡过去,谢徴绘了一张符塞进他的掌心里,趁着那双眼皮要闭上之前,握住他的手心说:“此前你叫我为你看手相看你未来好不好,太乌!我不曾告诉你,你的来日太好太好了!前程锦绣!风生水起!必然能够安享晚年!”
破布悠哉悠哉的跟过来,不轻不重的“啧”了一声:“再多具体,年轻人你怕是要吐血了。”
谢徴没听着叫姚圣珊听着了,不过他今日没心情搭理一块破布似得老东西,只专注跟着谢徴,问道:“储上昨日离开时就已经布局了?太乌是如何救下的,大军怎么一晚上就穿过中州城将皇宫围了?臣……”
谢徴看过去。姚圣珊顿了顿,眉眼一舒展:“翟玩,关照。”
“他二人是预院良才,在对方轻敌之下领兵潜入中州城将关哨除掉,救下太乌并不是难事。”谢徴一面和他说着,一面吩咐人把太乌抬下去救治,“魏仁择想要看我的选择,我退了。但有的事,本不用我亲自来做。”
“退即是进。”姚圣珊觉得很妙,“储上比臣想的要通透。”
谢徴一笑:“你莫不是觉得我说了不带兵卒进城便真的会践言如初?”
姚圣珊道:“昨日是这样想的。”
“圣珊,我们对面的人是魏仁择。”谢徴道,“他曾教我像他一样,不拘君子,为胜,可出尔反尔,可不折手段。”
“于是他就用我教他的手段,出尔反尔,不折手段。”
宫墙之上一幅紫袍迎风狂吹,穿它的人两鬓在一夜之间全部斑白了。魏仁择居高临下的注视着宫墙外黑森森的数圈兵马,放声大笑。
“舅舅。”
黄袍加身者坐在四轮驱车上,被太监推着缓慢到魏仁择身侧。魏仁择应声回头,关切地责备:“陛下,此处风大,你应在殿内服药熏香歇息才对。”
阿兰因这样如常的语气而有一瞬间失神,恍如他们还有明日似得,他这幅病躯还需要好好珍重去等明日的太阳吗?舅舅还这样以为吗?
阿兰比起数月前要消瘦的多,和一年前没什么分别。一年前护法被请到中州为他炼制延年益寿的丹药,阿兰故而丰肉生血,预准千岁不死。
然而两月以前炼丹的护法忽而下落不明,有人传是死在了邑州,也有人传是找到了儿子远走高飞了,总之阿兰的药快吃尽了,他感受到力气在渐渐的失去,感受到舅舅日益怒火的增长,感受到太医院面如死灰的一群太医怕死的颤抖,也感受到他在靠近。
昨日听说谢徴因为一个昆仑奴而停止入城,阿兰简直心如火烧,他想命人把昆仑奴抓来看一眼找原因,却被舅舅阻止。
魏仁择道:“这陪他出生入死的饵能多挡一日,你就能多活一日,他须得钉死在那条街上不可。”
阿兰问:“陪他出生入死,就能让他这般在意吗?”
他想到曾在邑州天晶矿所遇之难,谢徴背他走出大山,说的是“救一人与救一万人,于孤而言都是无上功德”这种匪夷所思的话。阿兰自昨夜便不禁一万次的遐想,如若当初是谢徴遭遇不测,是他背着谢徴走出大山,那么或许就好了,那么或许在谢徴的心里,他阿兰也会占据无法撼动的一席之地。
因为谢徴这个人,他是不看身份的。
“陛下。”
“舅舅。”阿兰应道,“你说他什么时候来?”
魏仁择则眯眼,自顾自笑:“你说还有谁能替你拦住他?”
阿兰沉默。
魏仁择闭上眼,双手背负:“舅舅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