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读小说>领证可以结婚不行 > 4050(第10页)
4050(第10页)
陈嘉弼说得对,陈广海刻薄阴毒,把自家侄女说得如此不堪,董只只此刻相信,陈嘉弼带姐弟俩舍弃家业,逃出魔窟,是件无比正确的事。
她不愿与这种卑鄙小人多接触,转身离开,换个安静的角落待着。
手腕被粗糙的掌心抓住,董只只扭头,余光瞥向四周,按捺内心焚烧的怒火,清冷笑道:“陈总请自重,您也不希望把自己的宴会搞砸吧?”
言语侮辱,对方无动于衷,这让陈广海很没面子,他的场子,他说了算,松开董只只,继续挑衅:“你两个弟弟,一个在韩国当练习生,一个在北京念大学,我没说错吧?”
“你想怎样?”董只只心里咯噔,他消息倒是灵通,护犊心切的董只只用冰凉的眸子直视他,用力抽回手臂,原地站定。
过了很多年安稳日子,董只只几乎忘了有陈广海这号人。自陈九堂孤身离开青岛,再没打扰过姐弟三人生活,她以为这事翻了篇,未料他们的一举一动,尽收陈广海眼底。
他究竟想怎么样?
心底的不安,在体内蹿腾,董只只闭紧嘴,不想被他看出牙齿在打架。
一方面是愤怒,另一方面是害怕。
陈广海可不是绅士,他是豪取抢夺的土匪,恃强凌弱是他赖以为生的手段,一个小辈敢在他面前大声嚷嚷,还恶狠狠地盯他,必要给她点颜色看看,他阴笑道:“我没别的意思,就想提醒你,别觊觎陈家产业,这些和你,还有两个弟弟,没半毛钱关系,任何人休想动它脑筋,包括那老东西。”
只有弱者,才会放狠话,强者无需打没有意义的嘴仗。
董只只就是踏着这条道走来的,工地上解救陈嘉弼,胡同里带走陈鼎之,无一例外。
可陈广海已经得到他们全部家产,又在害怕什么?
老东西——
他指的是陈九堂,关系再怎么不睦,他到底是陈广海父亲。姐弟三人是他的血脉,保护小辈是理所当然。
所以陈广海明知三人下落,这些年并未打扰到他们。
他顾忌的不是董只只,是陈九堂。
想到这里,董只只忽然镇定下来,提高声线,哼哼两声:“动我弟弟,你试试看?”
“给你脸了?这是和长辈说话的态度?”陈广海被激怒,手一甩,杯里红酒泼出去。
董只只没料到他当场失态,下意识扭头闭眼,抬起手臂阻挡。
刹那间,手背被什么人拽了下,重心不稳,往后踉跄两步。
睁开眼,一个欣长的黑影,覆在眼前,像一堵墙,将她与危险阻隔开来。
红酒飞溅而来,从肩膀两侧划过,只有几滴落在她的发梢。
董只只安然无恙。
她回过神,目光游移,边上是莫少楷,单掌托在她后背,关切询问:“还好吗?”
董只只重心往前移一移,扭几下手腕,摇了摇头:“没事。”
相比拉他出险境的莫少楷,董只只对身前的背影,更加好奇。
定目细看,白色运动衫背后印了四个大字——北京大学。
陈嘉弼落下张开的双臂,回头瞥一眼,她担心姐姐安危,然而视线很快从董只只只沾几滴殷红的面颊划走,转而看向身边的莫少楷,见她用手帕在姐姐脸上擦拭酒渍,眼中燃起妒意。
眼下不是解决情感纠纷的时候,他们有共同的敌人要对付,陈嘉弼抹一把脸,避开董只只方向,甩几下头发,又把头转回去。
陈嘉弼冷笑道:“二叔,几年没见,你怎么还这么鲁莽,靠不光彩的手段,夺我们家产,是想赶尽杀绝?有本事冲我来,敢动我姐一根头发,我让你今天横着出去。”
说着,他抄起餐桌上一张空盘子,在桌角一磕,“哐当”一声,拿着残片指向陈广海。
他以为这样做,会引起会场骚乱,有人站出来为姐弟俩撑腰,口诛笔伐,指责陈广海霸占兄弟家业的卑劣行径。
可惜他终究算错一步,这里是香港。
豪门狗血天天上演,这点破事,宾客见怪不怪,没被他的狠劲吓到。
相反,一个个冷眼旁观,像是在看热闹。
陈广海不是香港人,与他们毫不相干,不过是来捧个场,没什么交情可言。
自己秘书受辱,莫少楷脸上挂不住,虽然不知这大学生从哪里冒出来,但这种嘴上斗狠,完全是隔靴搔痒,起不到一丁点作用,还会被人当成笑话。
果然,边上几名女子轻蔑地笑声,传了过来,根本没把一陈嘉弼的话当回事。
莫少楷轻声询问:“你认识陈广海?”
董只只点头,小声说:“他是我二叔。”
“我来处理。”莫少楷按了按她的手背,露出儒雅的笑意。
他拍拍陈嘉弼的肩膀,抽走他手上的陶瓷片,做个往后退的手势。
陈嘉弼不知此人是谁,但刚才护住姐姐,应该没有敌意。
董只只在身后拽陈嘉弼的手,往后拉。
莫少楷这人讲究老板派头,董只只是他秘书,当众受辱,必讨回公道。
她等着看好戏。
好戏是好戏,不过出乎董只只意料。
莫少楷清冷发问:“陈总,在香港,这么做,怕是不合规矩。”
陈广海是聪明人,“在香港”这三个字他听得懂,连忙堆砌笑意,跟他握手:“误会,一场误会,许久没见到侄女,有点激动,手滑,手滑。我不知道董只只是莫总秘书,还请见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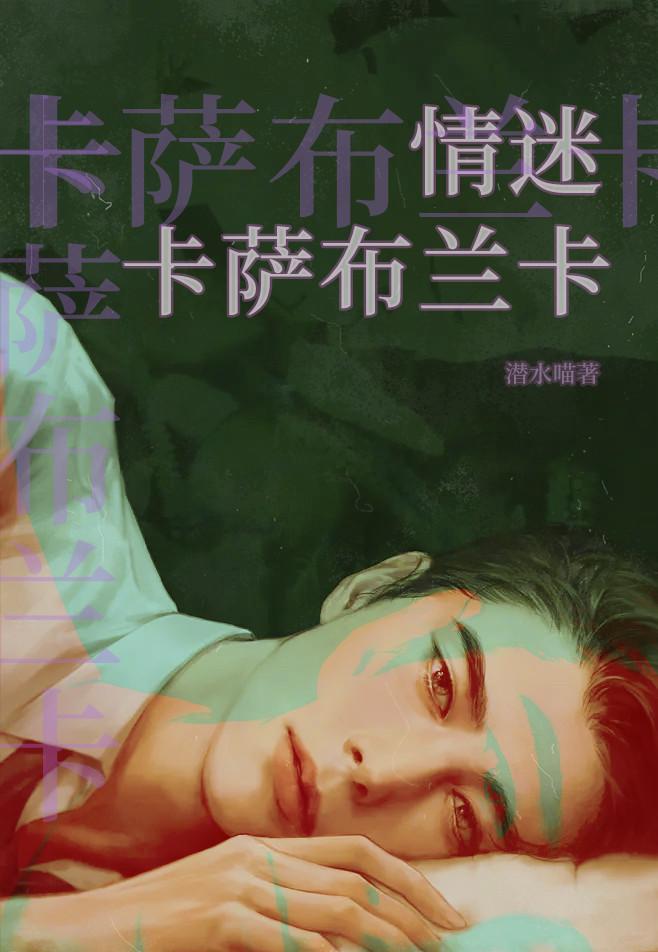
![(综原神同人)[原神]是木遁忍者不是草神+番外](/img/4015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