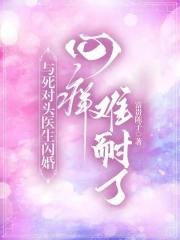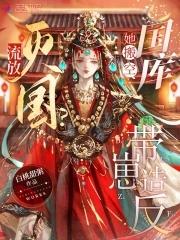我去读小说>当二凤崽遇上始皇爹 > 4050(第29页)
4050(第29页)
如果自己真活到一百岁,这孩子即位时都快八十了,一个太子熬到这把年纪才登基,那些臣子能服他的管吗?
而且,到时自己双眼一闭,孩子还不知有多伤心,一个快八十岁的老儿子,又得操持他的丧礼,又要忙着处理朝政,还要跟那帮大臣斗智斗勇不行!
只是稍稍这么想一想,秦王就知道自己根本放心不下。
世民从小就爱哭,又爱找他撒娇,将来,如果不多给孩子些时间慢慢过渡接受,他真担心自己前脚刚走,孩子后脚就伤心过度跟来了!
他情不自禁抱紧了怀中的孩子,暗忖着,太上皇这个建议,其实也是有几分可取之处的。
至少,单从名字来看,总比太上王要尊贵得多吧?
李世民听完这话,茫然抬起头看向父亲。
他只不过趁机这么随口一提,秦王就大有松动之意了吗?
前朝历代史书,多称秦始皇刚愎自用、独揽君权、连个太子都舍不得立,可谁能想到,他竟然这么好劝。
这可是在君王还活着时、就主动提前禅位的国之大事啊!
秦王却误读了他这小表情,轻捏着孩子的小手,挑眉冷笑道,
“怎么,不满意?你想让我现在就退位让贤?”
李世民忙挣脱手紧紧抱住父亲,依偎着他解释道,
“哪有呀,孩儿怎么会这么贪心!我还要看着阿父带领大秦一统四海呢,孩儿相信,你会成为大秦最厉害的王!阿父说得很对,这事还是等孩儿长大后再说吧。”
反正,他已经探出秦王的底线了。
秦王这才满意扬起了嘴角,这孩子虽然时常得寸进尺,却又很懂分寸从不贪心。
他正想夸一夸孩子,李世民突然想起一件事,急忙问道,
“阿父,赵国此次大败,秦国可会乘胜追击?”
秦王颔首,
“这是自然。桓猗全军士气正盛,正是一鼓作气攻城之时,朝廷如今正在调拨军粮,五月中旬,他会再带十五万大军攻打宜安。”
李世民心中一咯噔,脱口而出道,
“不行,这趟不能再让桓猗去了!”
“为何?你还担心他率军降赵不成?”秦王笑着刮了刮孩子的小鼻子,语气调侃道。
李世民的小脸却绷得很严肃,
“才不是呢!赵国这次的伤亡太过惨重,就算赵王再如何猜忌李牧,朝臣也一定会支持派他上阵来反击秦军。桓猗虽然十分勇猛,性子却冲动易怒,孩儿以为,这回该派最沉稳的王翦率领大军前去对阵。”
秦王轻蹙眉头沉思起来,
“王翦?不可。上回的平阳大捷,乃是桓猗带人打下的,寡人若贸然改换王翦攻打宜安,恐怕朝中会生出各种猜测,桓猗也会心生不满”
因为,宜安也归属于平阳,按照惯例,如果将领没有犯下大错,朝廷就不会中途换人抢功。
李世民想了想,灵机一动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叶腾那日不是说,他会在五月中旬献城给我们吗?到时秦国也要发兵过去接收,不如就让桓猗去吧。”
秦王有些奇怪地看着他,
“桓猗先前也跟李牧数次交锋过,对方防守虽十分厉害,秦军却也能跟他打个僵持平局,你为何如此担忧宜安之战?”
李世民紧紧皱起眉头,
“因为骄兵必败,这一趟,跟以前的局势完全不同啊!桓猗刚刚斩杀了赵军十万人,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以他的性子,必会放松警惕。
而李牧面对如此大仇,他带军复出的第一战,必会想尽办法剿杀秦军、以重振赵军士气阿父,孩儿以为这一战事关重大,只有王翦带军才是最稳妥的!”
秦王认真思考了一会儿,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确实有几分道理,我儿的兵书倒是没白读。当年长平一战后,三十万燕军趁虚而入想攻下邯郸,却被廉颇带着愤怒的数万赵军一路反攻,最后甚至打到了燕都蓟城,可见哀兵必胜啊。”
而李牧的战力有多凶悍,秦军早就领教过了,领着哀兵的他,若是对上领着骄兵的桓猗这一仗,确实对秦国大大不利!
说完,他立刻吩咐人召王翦和桓猗前来。
李世民悄悄松了一口气。
按照史书的记载,这趟本该发生在秦王十四年的宜安肥下之战,会以李牧成功为赵国复仇、斩杀桓猗和十多万秦军结束!
他前世悉心研究过历代将领的用兵特点,对王翦的风格也了若指掌:
此人从不贪功冒进,发兵前必会先治粮道、勤操士卒、稳固后方,以“先胜后战,谋而后动”的沉稳耐心,静待最合适的时机。
正因为这样,极擅示弱诱敌、事先设伏、奇计百出的李牧,后来在对上稳如泰山的王翦时,战事才会持续陷入胶着之中——
然后,他就死在了离间计里…
想到离间计,李世民忽而心中一动,想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如果没猜错的话,郭开上回行了个一箭双雕之计,一边把李牧派来赎人,一边派人秘杀了赵高。
他这么做,无非是想借机嫁祸李牧,一举除去两个眼中钉。有他在一旁设局进馋,赵王真会再派李牧上阵吗?
不,以赵王妒贤嫉能、提防武将的心性,如果李牧这趟真上了战场,那才叫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