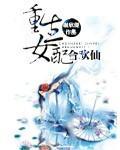我去读小说>权势巅峰:分手后,我青云直上 > 第22章 权衡(第3页)
第22章 权衡(第3页)
“大三时有个企业老板想通过我拿到徐老师对某个司法解释的学术意见,开价五万。我拒绝了,并报告了导师。”
“为什么拒绝?”
“因为那家企业涉嫌污染环境。”
郑仪语气平静。
“徐老师常说,法律人的脊梁一旦弯了,就再也直不回来。”
程安书没有表现出对郑仪回答的满意或不满,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他并不完全相信这世上有毫无破绽的人。
但在郑仪的故事里,他至少确认了一个关键点,这个年轻人足够聪明。
聪明到知道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聪明到明白有些诱惑背后往往藏着致命的陷阱;聪明到哪怕拒绝,也会给自己留好退路。
程安书了解过郑仪的家庭背景。
普通农家出身,父母靠种地供他读书,大学四年全靠奖学金和勤工俭学。这样的条件下,面对五万元的“举手之劳”,能够果断拒绝,本身就说明问题。
“徐永康教学生的本事,我是服气的。”
程安书似笑非笑地看了郑仪一眼。
“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时拿了那五万,现在会怎样?”
这不是假设,而是最后一个隐晦的警告。
郑仪直视程安书的目光,声音沉稳:
“那家企业去年因为污染被查封,老板行贿的案子牵出十几个干部。如果我当时收了钱,现在应该和他们一起在服刑。”
程安书的手指在沙发扶手上轻轻敲击,节奏缓慢而规律。
客厅里一时安静下来,只剩下钟表的滴答声。
终于,程安书站起身,意味声长地说道:
“年轻人有原则是好事,但官场上最忌讳的就是非黑即白。王振国欣赏你的锐气,我期待你的韧性。”
程安书走到书柜前,从抽屉里取出一张名片,递给郑仪。
“这是我的私人号码。”
简单的七个字,分量却重若千钧。
在官场上,领导的私人联系方式从来不是轻易给出的。
这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认可,更是一种隐晦的承诺,日后若有需要,可直通此门。
郑仪双手接过,慎重地收进西装内袋:
“谢谢程叔叔。”
称呼已经从“秘书长”变成“叔叔”,这是双方默契的转变。
程安书满意地点点头,又看了眼墙上的挂钟:
“时间不早了,小悦,送送郑仪。”
程悦送郑仪出门,月色正好,照亮了家属院的小径。
“我爸很少给人名片。”
她轻声道。
“他看好你。”
郑仪望着远处岗哨的灯光:
“是因为今天的发言,还是因为我‘清清白白’?”
“都有。”
程悦停下脚步,直视他的眼睛。
“但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你和王振国并非完全一路人。”
这句话印证了郑仪的猜测。
程安书与王振国之间,不是对立,而是互补。
一个主攻,一个主守;一个锐意改革,一个稳控全局。
而自己,恰好具备双方都看重的特质。
这才是真正的橄榄枝。
不是简单的站队,而是成为连接两端的桥梁。